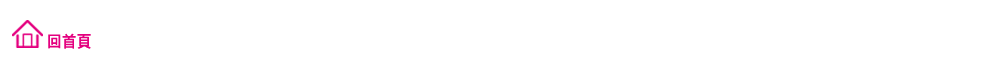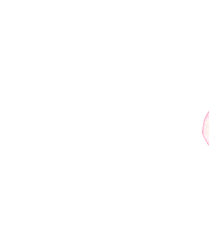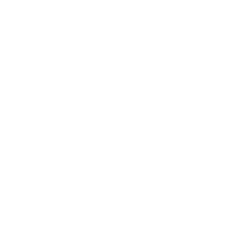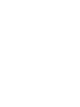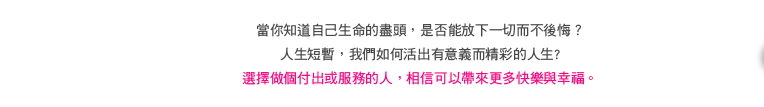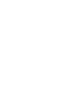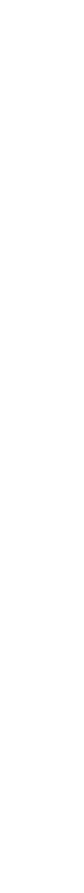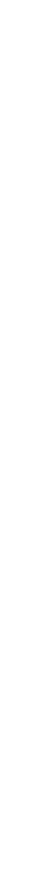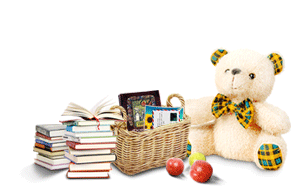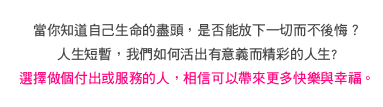

〉從「純真好奇」到「偏見與歧視」
許多小男孩愛火車,我家孩子也不例外。我偶爾會帶他去高鐵台中站區,搭一小段接駁的區間車往返高鐵站,小小鐵道迷往往就能樂上一整天。
這天,當我與孩子信步走在站區內,恰巧有個身形高䠷、約莫20歲的女孩走過身旁,孩子不自覺一直望著那位皮膚白皙到接近透亮的姊姊,沒有說話。
那是位白化症女孩。因為專業領域的關係,在我求學與工作生涯裡,認識好多位白化症的朋友或個案,所以於我而言並不陌生、亦不罕見;但對孩子來說,是他第一次遇到。

大姊姊注意到孩子看著她,大概也習慣這樣的注視,臉上始終掛著微笑;因為比起許多成人不友善的眼神,孩子單純的好奇,善意多了。等到穿越我們身旁往前多走了幾步路,她才回過頭來,刻意保持了一個很有禮貌的距離,對孩子揮揮手;但從孩子看著我的眼神,我感覺到:他遲疑了。
我心裡思忖著:面對一個三歲多的孩子,他真實感受到外觀的不同而產生了困惑,我該用什麼樣的語言幫助他理解、回應與靠近眼前這位白化症女孩?
「你記得媽咪跟你說過白雪公主的故事嗎?」我問,他點點頭。
「故事裡,有幾個白雪公主呢?」
「一個。」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接著問,「那你知道白雪公主為什麼被叫做白雪公主嗎?」
「因為皮膚像雪那麼白。」我知道,這是他從故事書裡看到的圖像與描述。
「你覺得那位大姊姊像不像白雪公主?」他看往女孩的方向,再看看我,眨著圓滾滾的大眼睛,點頭。
「剛剛白雪公主姊姊跟你打招呼耶!你想不想也跟姊姊打招呼?」我話一說完,顯然孩子已少了許多疑慮、多了幾分篤定,直接拉著我的手往女孩的方向走去。她似乎對孩子的舉動感到些許的意外,臉上閃過一抹詫異的神情,瞬間即逝。
接著,她蹲下身子、使自己與孩子等高。我在心裡很是激賞:這麼細膩與體貼的動作,連我與孩子互動時都偶會忽略、需要常常自我提醒,但她卻做得如此自然。我想,唯有深刻感受過「站在對方位置/高度看世界」的溫暖,方能如此貼近。
她伸出右手,對孩子提出邀請;這回孩子全然沒有遲疑,也不再回頭「請示爸爸」可不可以,很快地就跟姊姊如話家常般地細數他剛剛所看見的火車種類與名稱。
孩子對於明顯可見的陌生事物,反應往往很直覺、也常流露出真誠而單純的好奇。猶如白紙般的心靈,可以在成人的引導下,學會如何尊重、靠近,與正向理解;但,在我們的「示範」下,他們也能很快地學會「偏見」或「歧視」的視框。
這些視框及其衍生的行為反應,對於外觀上有顯著不同的罕病朋友而言,是種赤裸裸、難以遮蔽的傷害。
而有別於這種赤裸的傷害,Sherry從小到大所經歷的,是另一種辛苦、另一類的痛。
〉Sherry:如果可以,衷心期盼遇到一個更願意接納與理解我的老師
Sherry有家族遺傳性的「法布瑞氏症」,全家族共有十餘位成員罹病。因家族裡有其他家人先發病,所以自國小開始她即被列為追蹤觀察名單,但直至國中才確立診斷。雖然身為女性的她,臨床症狀比男性患者輕微,但光是如此,已足以令她的成長過程倍感艱辛。
「患這種病,身體常常沒來由的劇烈疼痛、體力不支,無法專注學習不說,甚至連到校都有困難,在尚未確診之前,常常因此被老師與同學誤解是逃避課業壓力、故意找藉口不上學…到後來,連我都開始懷疑起自己是不是真如老師說的這麼糟。」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眼眶已經溼潤。
身為教育工作者,看著眼前的Sherry及其所說的這段話,我不禁在腦海中無數畫面裡搜尋:是不是曾幾何時,我也成了學生心裡那位「被期待願意多些接納與理解的老師」而不自知?
「沒想到,進入職場以後,由於我們外觀上大多與一般人無異,但因為時常需要請假接受治療或休養,所以依舊得面對同事對工作能力、敬業態度、公平性…等質疑,難以被理解與接納,幼時的那些經驗感受,彷彿都回來了。」她拭去眼淚,打起精神,繼續說,「但我真的非常感謝社會福利政策對我們工作權的保障,我很珍惜、喜歡這份工作,有自信做得不比其他人差。」
〉彭小姐:接受治療,我或許還可以活五年;但自費治療,我們全家撐不過三個月
除了Sherry所提到的「工作權保障」外,社會福利政策對「家有罕病患者家庭」的重要性,更超乎我們想像。這一點,罹患「肺動脈高壓症」的彭小姐及其家人,尤感深刻。
「當我聽到主治醫師每天把『只剩下五年壽命』掛在嘴邊,我以為已經夠令我絕望了!沒想到,更讓我絕望的是聽到治療過程『可能沒有健保給付』,我當場跟醫師說:接受治療,我或許還可以活五年;但若要自費治療,我們全家絕對撐不過三個月。」她的情緒激動,語氣略帶顫抖。
從Sherry與彭小姐的病史看來,雖然她們的病症與大多數罕見疾病一樣、皆源起於基因變異,但卻都不是一出生即發病,甚至彭小姐還是在年近半百時才意外發現自己竟然罹患了這麼罕見的病症。在這之前,她們跟許多罕病的患者一樣,渾然不知自己的基因變異、是潛在的病患,直到發病的那一刻。
這背後象徵的意義是:也許當我們高談闊論著「健保資源應花費在刀口上、追求大多數人的身體健康,而非少數的罕見疾病」時,其實我們自己以及所愛的家人,可能正是某種罕見疾病的潛在患者,只是尚未發病而已。
那麼,關於「健保資源應否投入在罕見疾病的治療」之議題討論,您是否願意加入一些對人與生命的同理、關懷、溫度,就像對自己與家人那般,然後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與立場?
〉關係與支持:藥物之外的心靈藥方
「活著,才有機會遇見更美好的事物。」這是茶會結束前,Sherry與大家分享、令人動容的一句話。
自在呼吸、大口喝水、走路出門、享受陽光日照…這些於我們而言理所當然的存在,對罕見疾病的患者來說,是種奢求。與疾病共處,是他們每天最真實的生活,永遠只能默默等待新藥物的問世,比現有藥物舒緩症狀、提高生活品質多些,卻不容許盼望「根治」。
他們可以輕易找到幾十個放棄生命的理由,但堅持下去只要一個理由:擁有穩定的關係與支持系統。
無論Sherry或是彭小姐,在她們對自己、對未來陷入絕望之際,「良好的醫病關係」與「伴侶/家人無條件支持」無疑是撐住她們的力量。前者安頓了對病症不安的心,後者則承接了生活中每一個沮喪的時刻;很殘酷,卻也無比真實。
誠如彭小姐的先生所說:「太太剛發病的那一年,我彷彿忘記『怎麼笑』。」患者與家人的辛苦可見一斑。所以當Sherry決定開口與當時還是男友的先生袒露自己的健康狀況之前,問了好多假設性的問題,探問對方的態度以決定要不要說,甚至評估關係要不要繼續下去。
「我一直都很感謝我的先生不只樂觀、也不是『媽寶』,與他的父母界線清楚,有個具有擔當的肩膀可以讓我依靠,一起面對我的病症。」Sherry的臉上漾起淡淡的、幸福的微笑,「所以,我也很謝謝我的智囊團,若非他們一直告訴我『妳也不賴啊!有更好的(對象)可以選,為什麼要委屈自己?大不了就打回原形、回到一個人』,讓我知道我也有愛人、挑選伴侶的權利,否則我哪有機會遇到他?哪敢奢望擁有自己的幸福?」
「罕見的,究竟是『疾病本身』,還是『好好活著與追求幸福的權利』?」在微涼的夏日午後、聚會結束前,我的心裡忍不住升起一陣疼惜。